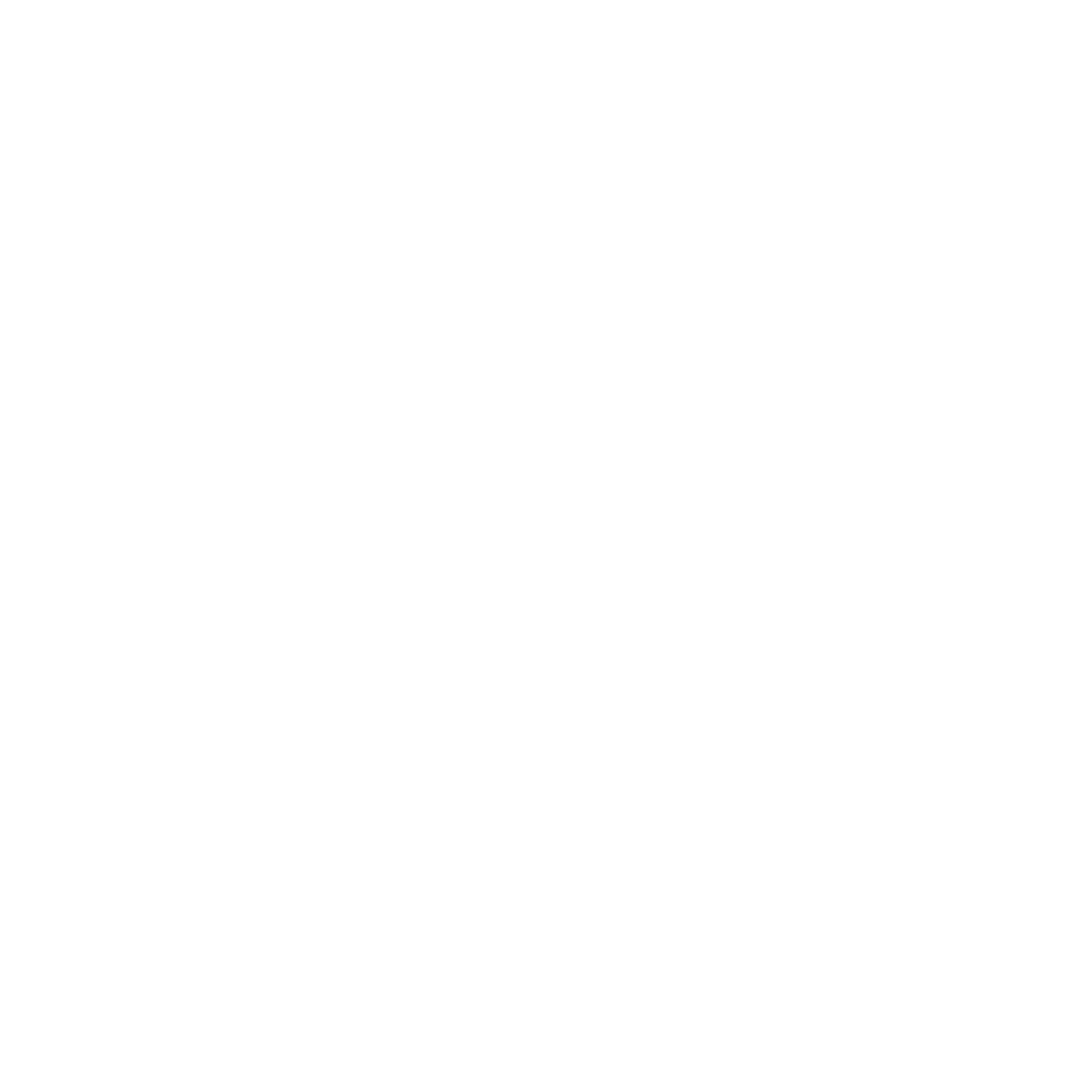一篇流水账————那些流经我的回忆-13
与阿泠(六)
今天是六月七号,星期五,天气多云转阴。按照安排,今天是学院一年一度的毕业季“草坪音乐节”活动,很久之前就听说这个活动正在被筹办,于是早早报了名——我打算在这天弹唱赵雷的《程艾影》。此外,在一周前,我还接了另一个活——主持人。 但这次不一样,学院打算“买一送一”,于是,阿泠也凭借毕业生的身份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我的搭档(事实上,毕业生的身份因素不占大头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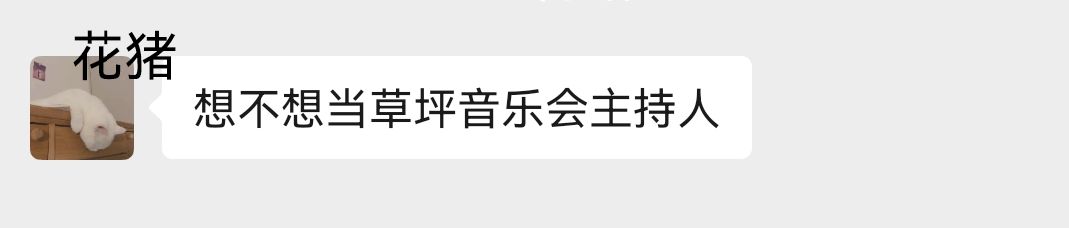
《程艾影》是一首情歌,从歌词就能看得出来。我的表演略显尴尬:先是因为自重不断下坠的话筒支架,我不得不用腿挡住他以防话筒掉下来砸坏听众们的耳朵;后是因为腿部的疲惫而逐渐变形的气息;再然后,是忘词(检讨!我讨厌一切需要背的东西)。

但这些都不重要,重头戏在于我准备下场时。作为主持人的阿泠阻止了我下台,临场发挥了一段:
“哎,先别急着下台,我们还有个采访环节。你觉得,今晚的活动中,是什么让你心荡漾呢?”
“当然是你呀!”
我是个i人,但是回答阿泠时没有一点犹豫,这或许会是我转e的流程之一?
.png)
河西走廊是地球深陷的眼窝
“青藏高原是地球高高隆起的额头。”在印象里,曾经在毕淑敏的《阿里》中读到过这样一句话。她这样想象,明显是把地球比作了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农,虽历经风霜,却也保有智慧的象征。河西走廊离青藏高原不远的,在中国的版图上同样位于西端,我想河西走廊应该是位于这个老农的眼睛吧。可这双眼睛不是那么澄澈的,毕竟它受惯了风沙,顶够了风霜雨雪,也遭受了不少人的冷眼。就真的像是一个老农的眼睛,着了风就轻易流泪,然后泪水顺着因为干燥气候而产生的皲裂淌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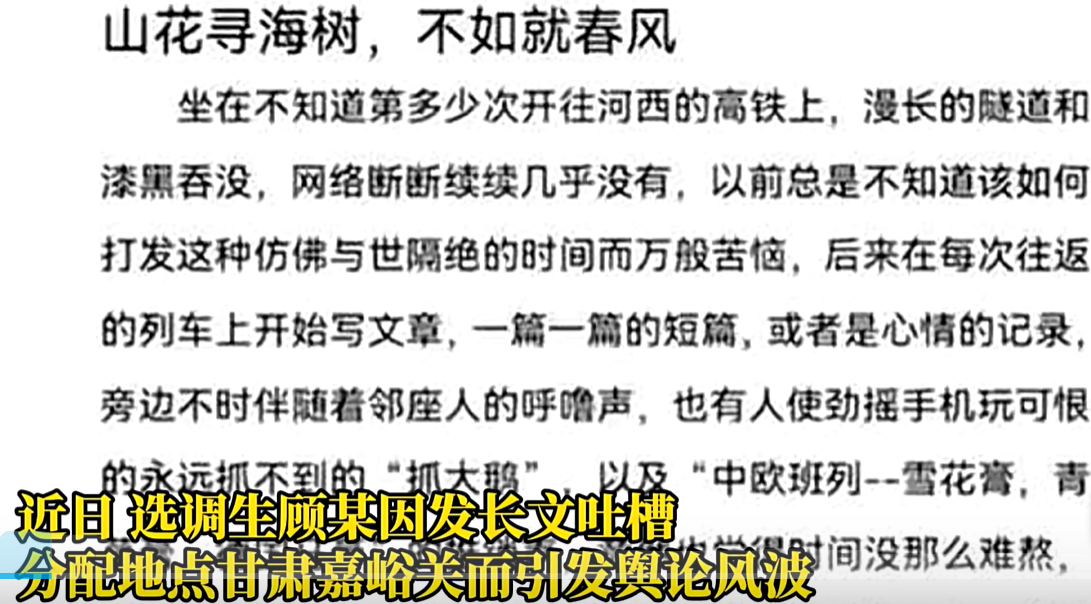
这个老农的眼睛并不那么引人瞩目,比起北上广深又或是成渝兰这种耀眼的明珠来说,它们简直太普通了,你甚至可以说它们太过于务实,以至于看不见远方有什么,毕竟从里面你只能读出黄土和蓝天,以及一种矛盾的期待——这种期待在河西走廊的几个城市随处可见。我是酒泉人,离嘉峪关只有12公里的距离,相当于在成都跨一个区,我高中时同桌的父亲就是这种老农的形象。我永远忘不了他耳朵上因为干燥和低温而产生的裂纹,里面嵌满了黑色的泥土,我也忘不了他对孩子的期待,期望他有朝一日能考出河西走廊,远走高飞。父亲在期待着孩子通过高考出人头地,所以勤勤恳恳地耕地,即使是大年三十,即使是零下20度的气温,他还是开着家里的大卡车来菜市场卖白菜,偶然看到我后,不由分说地往我怀里塞了几棵大白菜。
回忆到这,我有点后悔。看见网上有人将通向河西走廊的火车比作囚笼,说乘客们像是黑奴,又将前往嘉峪关工作的自己称为出卖灵魂的妓女,我有点后悔我没能站起来为家乡声援,因为那边的人都太好了,他们不应该被这样评价,贫瘠干旱的地方,人们在堂堂正正地活着,这就是西北戈壁上大多数人追求的东西。那样的火车我每年都要坐上几个来回,不得不承认那位选调生说的都是事实——乘客们打呼、抓大鹅,每当上了戈壁就没网……我们是养尊处优的一代,这些东西似乎已经难以承受,但不该丢了对他们的尊重,那些坚守戈壁的人们从来都不落后。
我希望那双眼睛流泪时,不用所有人都可以擦去那些浑浊的泪水,但至少应该收起鄙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