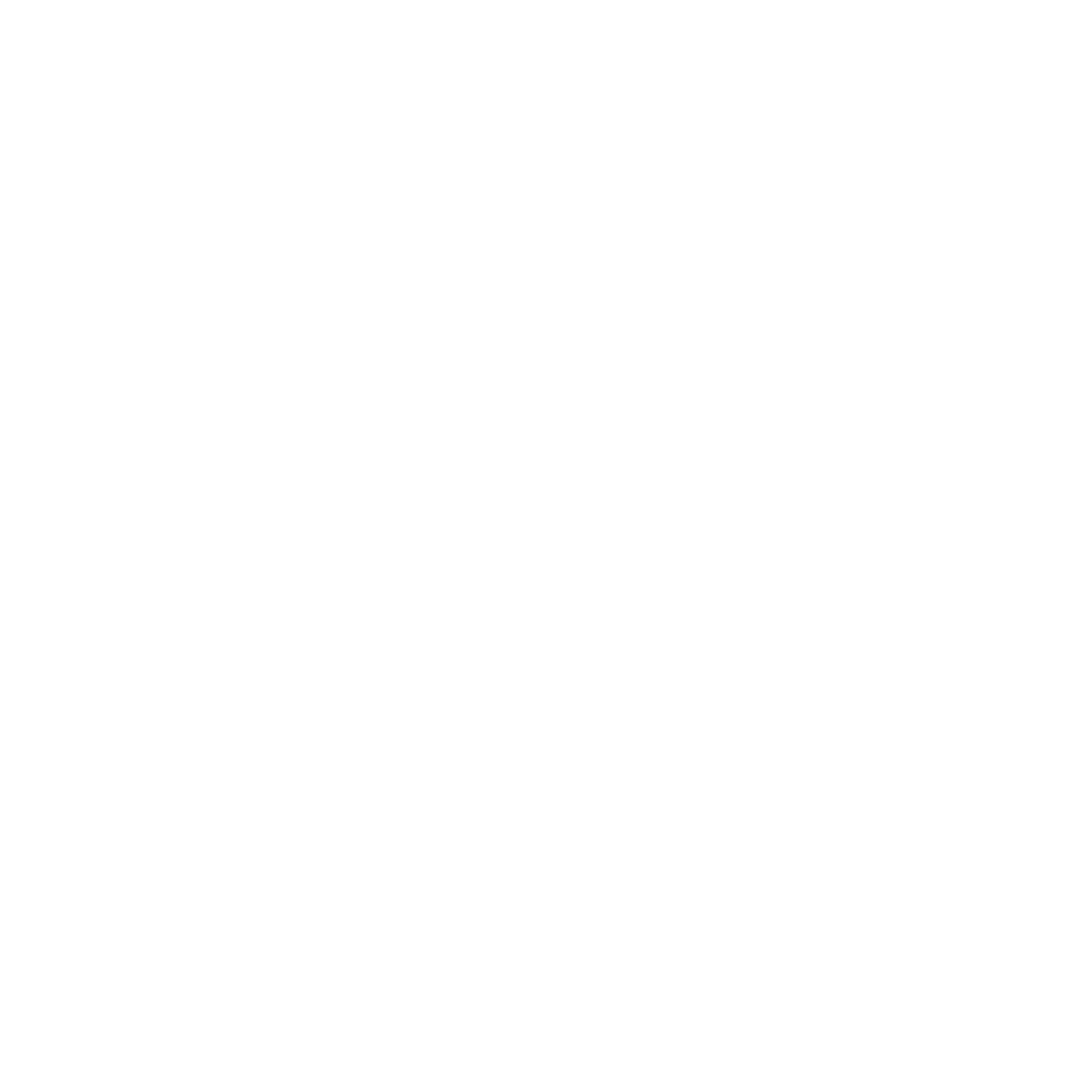一篇流水账————那些流经我的回忆-18
又说到雨
十月一日,十月二日,周三周四。连续两天阴雨。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凉,这话一点不假,自几天前狂风骤雨之后,气温明显没有那么放肆,反而日渐收敛了下去,逐渐开始冷了。


这几天的活动?仍然还是加班,偶尔趁着摸鱼的间隙翻翻手机,几乎每天的朋友圈都有来自祖国各地大好河山的照片——甚至也有国外的。这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件好事,毕竟足不出户,不用人挤人,就看到了广西的山水,甘肃的烧烤,乐山的雾气,斯里兰卡的小鹿,澳洲的海岸线。
放下手机,抬头是神经网络进行到第8轮epoch的回显以及一篇论文,窗外就是雨。很多文学作品通常都会把许多痛彻心扉的场景与雨夜联系在一起:男女主的诀别、发现被背叛真相的主人公、舍身救局的英雄…总之作家们好像约定俗成,对雨夜有着默契的恨意,作别的人们通常会在雨最大时选择淋雨,然后将视角渐渐拉远,这样更不容易分清脸上流的到底是雨水还是泪水。也许是我在西北长大的缘故,那里常年缺雨,导致我对雨实在恨不起来。泥土的腥味,雨水掉落的声音,通常也意味着不再干燥的空气、不再酷热的气温——单凭高温这一点,我实在不喜欢夏天,但下雨可以带走高温。
晚上要顺便给电动车充电,回寝室时是散步回去的。塞上耳机,罕有人迹的学校,突然感觉整个世界都属于自己了。


给绝望的人以力量
假期所剩无几。去年十一假期刚刚开始时,我在芳草街市集买到了一款香薰,是基础款的茶香,味道清新淡雅,刚好可以盖住寝室里木头发霉的味道。前几天突然想起这个味道,于是决定回到老地方看看还能不能找到同款香薰,可扑了个空。


许久没有吃过东北菜,突然有些馋,某天下午突然拉着阿泠就去了东北饺子馆,吃了锅包肉,还又点了一份酸菜猪肉炖粉条。吃得撑,乃至路都走不动。

翻了翻公众号,看到一位语文老师在读《走出非洲》。书中讲,非洲的一些土著居民不喜欢规程化的事务,也不喜欢循规蹈矩,这让德国医生很头疼——因为对同一种疾病的治疗需要规程化的治疗手段。这位老师又讲,那些原住民通常为所有事情都做好最坏的打算,所以他们面对变故时才更加坦然。“这给绝望的人以力量。”他说。

秋天真的来了,偶尔调酒喝喝。这是一杯雪碧和杰克丹尼威士忌的混合酒,喝起来有一股木桶的味道。是时候收起夏衣,准备上秋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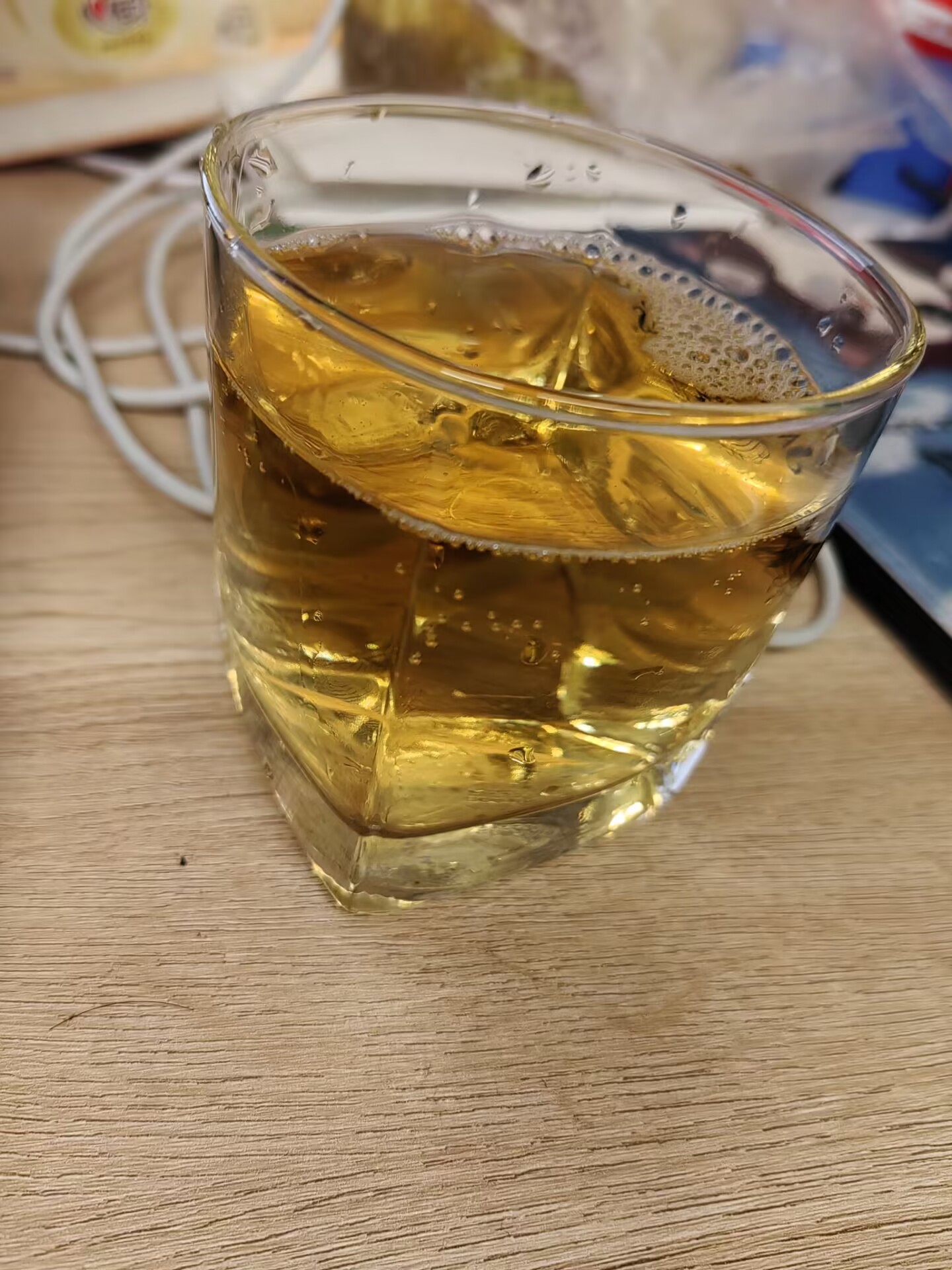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
十月七日,农历九月初五,再有一个月就是冬天了,很难相信成都的秋天开始才刚刚过一个礼拜。宿舍楼前的一座小桥下,开了一株花,也是高温被秋风吹走后的附赠品。今天是十月以来第一个晴天,阳光很好,晚些时候的夕阳很好看,紧急下班,叫上阿泠出门兜风。


晚上出门散步,耳机里又循环到了《边缘行者》的一段BGM,歌词充满了朋克风情,主打一个对权力和秩序的叛逆。可以说,在《赛博朋克2077》的世界观里,穷人的孩子们主打一个毫无顾虑,只因他们没有任何软肋——没房没车没存款,有时连命也不在乎,这倒也是一种做好最坏打算的准备:大不了一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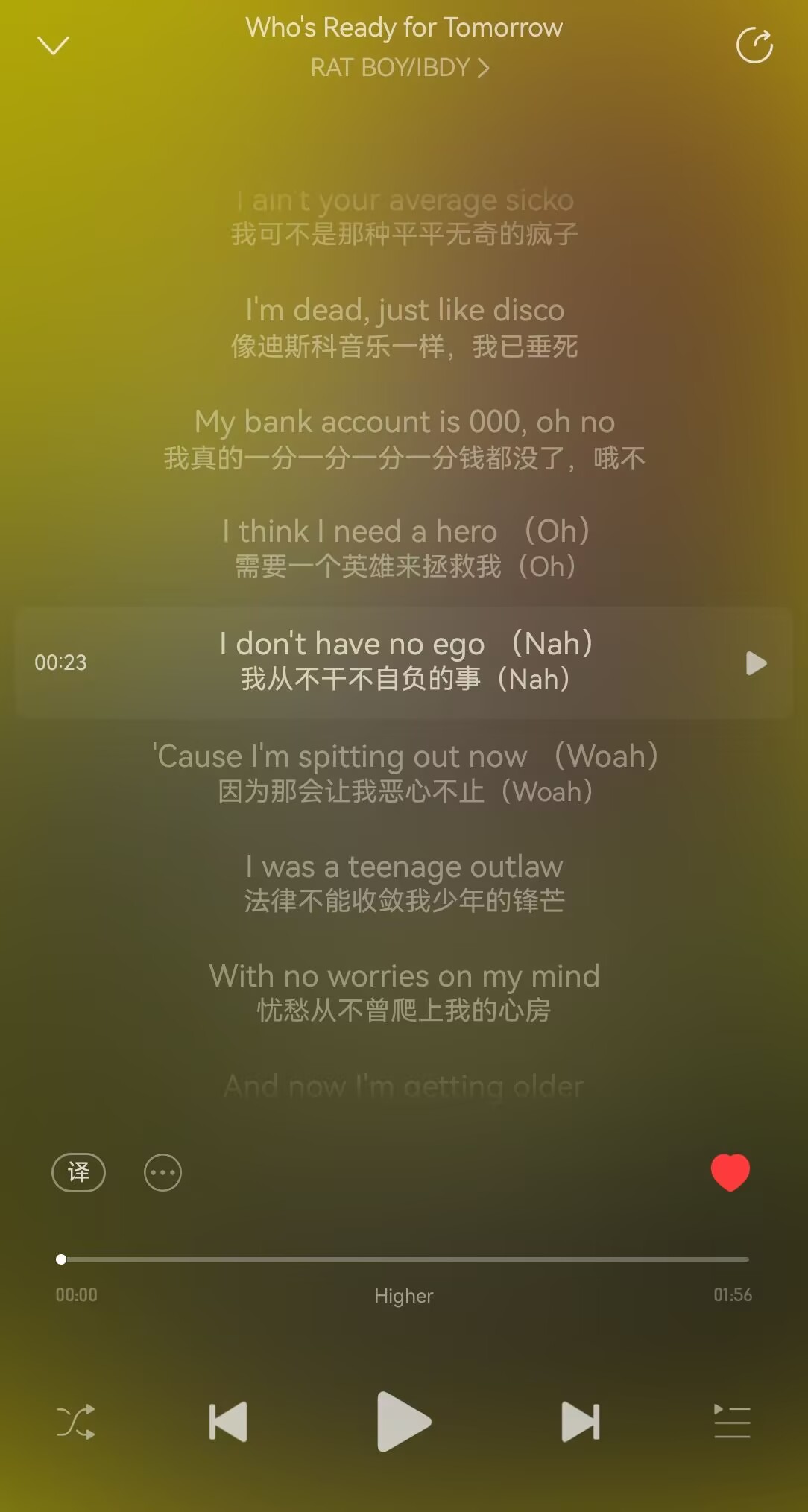
首都记
十月十日,农历九月初八,成都多云,北京晴。
因缘际会,借着出差的由头又去了一次北京。在母亲眼里,那是个好地方,对古代帝王来说是定都的良选,却又同时对北京人有点偏见:“北京人有点排外,自己注意安全。”我上次离开北京时约莫9岁,现在对那里的印象早起随着孩提时代家庭的印象淡去了——对小孩来说,有爸妈的地方哪里都是家。

去时路
这次出发走得匆忙,只带了工作需要的东西,好在导师及时为我操办了所有交通事宜。匆忙跟阿泠吃了午饭,打车从校出发,就近机场上了飞机,直奔目的地。令我没想到的是,飞机居然提供了餐食:蛋糕卷、两片熏肉和一个小汉堡。蛋糕卷中规中矩,抹茶味,中间是红豆馅;熏肉片还配了一些意大利面,自身的味道很咸,由于刚刚从冷柜拿出来,更加重了那种咸味;小汉堡中间加的是一小片淀粉火腿肠、一些生菜和沙拉酱。除此之外,为了让我做好夜间工作的准备,我还为自己配了杯咖啡。

飞机上总归上不了网,趁此机会,抓起之前借的《走出非洲》读。作者的农场里收养了一个原住民小男孩,因为作者的帮助,一直困扰他的脓疮病痊愈了,于是他就决定留下来帮助作者照看农场。之前看到老师公众号所说的“给绝望的人以力量”,其实就是再说这位男孩的生存哲学。“生活还能糟糕到哪去?再糟糕,大不了就是一死”。
到了北京,天气晴朗得难以置信。我发了一句朋友圈感叹,立刻就有人回复:“来自南方人的震惊。”

说说海淀
工作的地点在海淀区,四环线上。叫我说那里是个和成都双流有的一拼的地方:所有过路的人,无一例外,全都行色匆匆,自顾自行走;所有过路的车,都在法律允许的区间内以最大速度行驶;所有的路,除了便于行人行走之外毫无特点,没有烟火气。工作间隙同母亲通电话,她说这些人都是为了生活拼命的人。

印象里面,北京人好像确实并不都是友善好相处的。9岁那年为了给父亲治病,一家人直接在海淀区五棵松体育馆附近租了个小房间住下,那里距离301总院直线距离不超过500米。以现在的角度回忆,那个房间不会超过50平米,可小时候却觉得它大极了,因为整个房间居然可以放得下两张和我家里一样大的小床。邻居是个北京老太太,自我们一家搬来后,确实没少遭到她的白眼:早上出门太早,吵到老太太睡觉了,要被数落一顿;暂时把垃圾放在门口,被老太太看到了,也要被数落一顿。有时候从外面回来,甚至能看到老太太在她家阳台上站着,冷眼看你,多少有些让人不寒而栗。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和这个不怎么欢迎我们的领居一样。那时候正值2009年春节,那时候北京市区甚至还允许燃放烟花爆竹。我同一位开在那个小区里的小便利店的老板儿子成了朋友——他与我年龄相仿,我们又恰好有同样的爱好:放炮。记得那个春节我几乎没有为了烟花不够玩而发过愁,他家的便利店就是我们的后备弹药库,老板人也很好,有时还会送我糖果吃。
可是九岁的男孩哪是静的下来点年纪?还是那个春节,有那么一回,我把一些别人家里没有燃尽的鞭炮收集起来,放在一个塑料袋里。回家(为了表述方便,现在也可把北京的出租屋称为家)打开门的瞬间,我突然发现袋子里窜出了火星,我想都没想,立刻丢下袋子,两步躲到了楼梯间里,再然后就是连环噼里啪啦,声音在封闭的楼道里被放大好几倍。后面的故事嘛,就是领居老太太的一次大爆发,她愤怒地推开门,指着我的父母,斥责我们一家外地人不懂规矩,居然敢在楼道里放鞭炮。于是爸妈俩人开始手忙脚乱地收拾残局,同时还得不停赔不是。
那次我确实吓坏了,不过不是被鞭炮吓坏的。我以为爸妈会把白天受的委屈在晚上转移给我,可他们没有,反而称赞我的反应很正确。
一切繁华与我无关
暂时结束工作,大约晚上9点,我临时决定在赶去酒店之前去鼓楼看看——现在我对北京的印象还有一部分源于赵雷的《鼓楼》。
离工作的地方不远,索性决定坐地铁前往。北京地铁二号线总给人一种纽约地铁的复古感(我没去过纽约,对纽约地铁的印象来自以上世纪为背景的美剧或者电子游戏),站台甚至没有玻璃屏障。

能看得出来,鼓楼白天时确实是个拥挤的地方。整条街呈横向分布,鼓楼在中间,所有街道全线禁止停车,我能想象到白天游客在这排队过马路的场景,定然是人山人海。而晚上稍冷清,偶尔有人驻足拍照。我戴上耳机,放上赵雷的《鼓楼》,从后海一路沿着鼓楼大街走过,发现自己的手机和充电宝同时电量告罄,于是在这里匆匆拍了照,打车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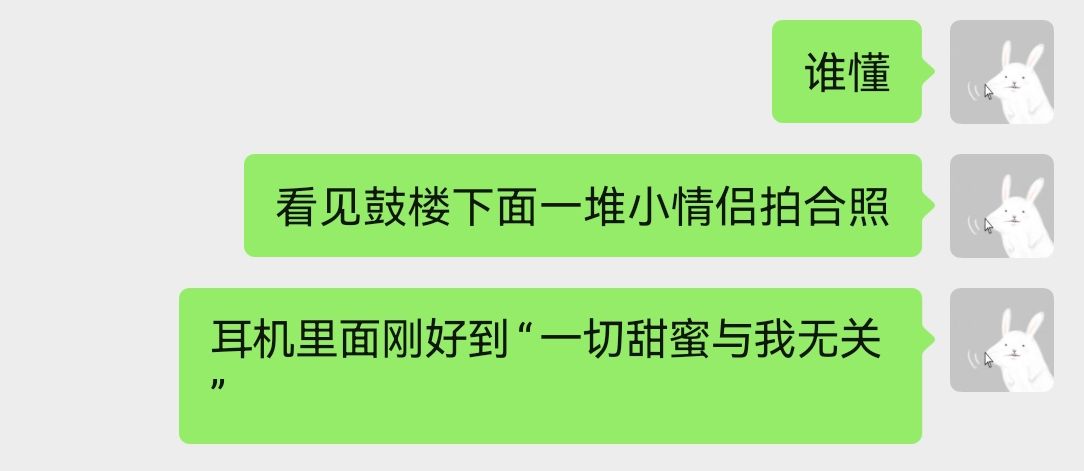
再说说交通
通勤,打工人永远绕不过的话题,在大城市打工,通勤注定要占去大多时间。这次来北京,除了去工作时做了地铁的机场专线与去鼓楼时临时决定坐地铁,其余通勤均靠网约车。不管哪里的司机网约车师傅,开车时都是一个字:野。从鼓楼出来后,打到的滴滴师傅是个北京本地人,开车章法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每个变线,每个路口都操作得令我心惊肉跳。我有如此深刻的感受,完全是因为手机没电了,想要问师傅师傅有充电宝可以借,没想到他当时就邀请我坐到前排,并拔下自己的充电口递给我充电。“先用我的吧,我的是快充。”我充了大约30%,就把充电线还给了他,我说,能应急就行。师傅听罢,随和地笑了笑。

第二天从旅馆赶去机场,同样还是坐了网约车。同样也是个北京大叔,不同的是,他的车上布置满了各种花,还贴有一些“加油、努力”之类的标语。“怎么样,北京冷吧?”令我意外的是,大叔竟然主动跟我攀谈了起来。我想起自己脑海中还有北京人“排外”的刻板印象,于是这两天同别人说话我都是在尽力模仿“京腔”说话的,但是和这大叔竟然一点也装不起来了。
”是啊,比成都冷的多了。“我没有瞎说,早上6点从酒店出门时,属实被个位数的气温暴击到了。
”你们南方人儿啊,一道深秋过来肯定受不了。头回来北京吗?“
”对,过来出差的。“我并没有说出我北方人的真实身份,可在成都惯了,抗寒的本事早不存在了。
”下次来,要记得穿厚点儿。要是11月再过来,北京的气温可就零下了。成都重庆再怎么说,也不会这么冷的。“
”是啊,最冷的时候也都在零上,到时候开个空调勉强还能捱一下。“
”嗐,空调那玩意儿也不怎么好用。北方这边儿都是用暖气的。再过几天,北京也就集中供暖了。“
……
”我之前也拉过俩成都的女孩儿。12月来的,一瞅咱这儿的树,光秃秃的,就跟我说,‘北京的树咋都死了哇?’可乐着我了。哎,你们成都那边的树冬天是不是都不会落叶的啊?“
”是啊,有些树会落叶,但大部分树冬天都还是绿油油的。不过下雪之后这些光秃秃的树上也就开始变得好看了。“
”哎,可惜啊。最近因为气候变暖,北京下雪就积不起来了。要是搁我小内时候啊,大伙还能凑一块儿打打雪仗堆堆雪人儿。“
……
”到了啊,拿好行李,过马路的时候注意安全,祝你一路顺风!“
”行,谢谢师傅啊,也祝你生意兴隆!“
归时路
下了出租车,一看表发现距离登机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慢吞吞地排完了安检,在首都机场内步行了约10分钟,还未找到登机口。一看才发现,登机口距离安检还有很远,甚至需要坐一次轨道列车才能到。这时我才发现提前一个多小时来候机的决定无比正确。

清晨的阳光非常好,一想到回成都后就很难见到这样的阳光,不禁觉得有些失落。在机场的便利店买了一块小蛋糕,打发了早饭,就直接登机了。


由于前一晚的酒店就在机场旁不远,因此我几乎被飞机引擎的动静吵得一宿未眠。上机之后发现提供了餐食,是牛肉汉堡。几口解决,然后开始补觉。

回来后,导师说这周末还有三个问题要解决。晚上,撑着伞出来散步,一边写下了这篇首都记。

写在后面
长大后有了接触更多人的机会,里面有不少北京人。本科的一位室友,长相与演员张译有一些相似;阿泠朋友的男朋友,一米九,敦厚可靠;广播站的直属学妹,随和爱笑……很幸运他们都不是”不好相处“的北京人。
地铁不是唯一的出行工具
10月19日,农历九月十七。周末,也是本学期以来度过的第一个完全没有加班的假期,但这并不是好事,这通常意味着导在这周刚好很忙,也代表着未来几天即将迎来一次井喷式的任务布置。

从文殊院到东郊记忆,坐地铁从一号线转八号线再坐8站就能到。听了母亲的建议,我决定坐公交过去,但路上并没有花费预想的那么久,算上走路去车站的时间,也比坐地铁少用了10分钟。

十月22日,农历九月二十。难得的晴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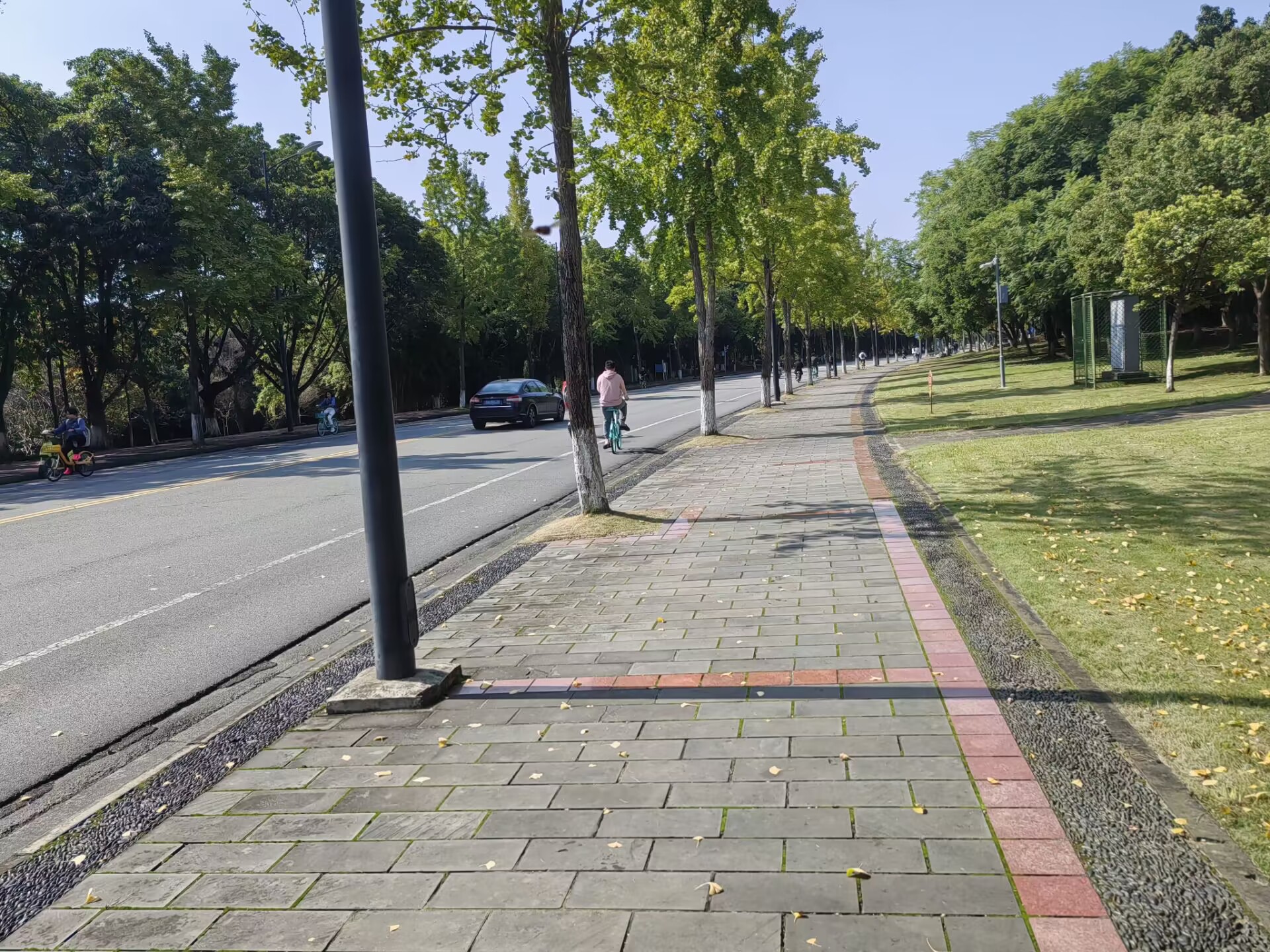

陈酿火锅
2003年,我29岁,在编辑部任职。也是那一年,我第一次走进了法庭,坐在被告席上。
那年冬天,老城区有很多火锅店,用脚步就能丈量的城市宽度竟然也能挤得下那么多家小店。那时候的火锅店煮锅大多用燃气,餐桌四四方方,刚好一边坐得下一个人,偶尔也有几个圆桌专供六人以上就餐。工作的地方就在小城市的某个角落,在老君庙公园前,在城区海拔最高点,我身边有很多刚从学校毕业,走出家庭荫蔽的年轻人,他们心怀正义感,怀抱理想,却也从不考虑做事的后果。这一点对于年轻记者来说,是一种大忌,谁知道无处安放的正义感会给初出茅庐的小牛犊招来多大只的老虎。
我坐在被告席上,局促不安,与我同行坐下的就是那个小记者,几天前,他的文章痛斥了老城区使用“老油”给顾客煮火锅的卑劣行为。老油者,乃是将食客们吃剩的火锅汤静置后浮于表层的清澈红油,如今被大众称为地沟油,一个意思。文章一经刊登,迅速引起轩然大波,曾经门庭若市的火锅店一夜之间变得无人光顾,顾客们唯恐避之不及,毫无疑问这对火锅店老板们来说是一次沉重打击,于是,这些火锅店老板们便联名将我们报社编辑部告上法庭。我看着在陪审团位置坐着的领导,怀着不安的心情,听法官下达了最终判决:我们需要向火锅店老板们郑重道歉,并在报纸上连续三期为他们的火锅店免费打广告。那时候啊,报纸几乎是人们了解外界的唯一媒介。
老油?确有此事。那个小记者做事确实冲动且不计后果。明访或暗访,他走访了很多家美味的火锅店,并亲自拍下了证据:店里的服务员亲手将两个桌子的残羹混在一起,倒在一个大塑料桶里。
可比起那段令人作呕的视频,我更加忘不了的,是法官叹口气后缓缓说出的一段话:“这些火锅店养活了很多人,一家店有店员20人,10家店就是200人,这200人背后还有他们的家人,这个数字再乘以3——600人。十年前他们从单位上下岗后,是这些火锅店重新给了他们生活下去的资格。救了他们,就等于救了600多人。”
我最终还是删掉了那些会毁掉他们生活的录像和证据。当然,火锅店后来执行了明厨亮灶的要求,代价是火锅的价格上调了原来的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