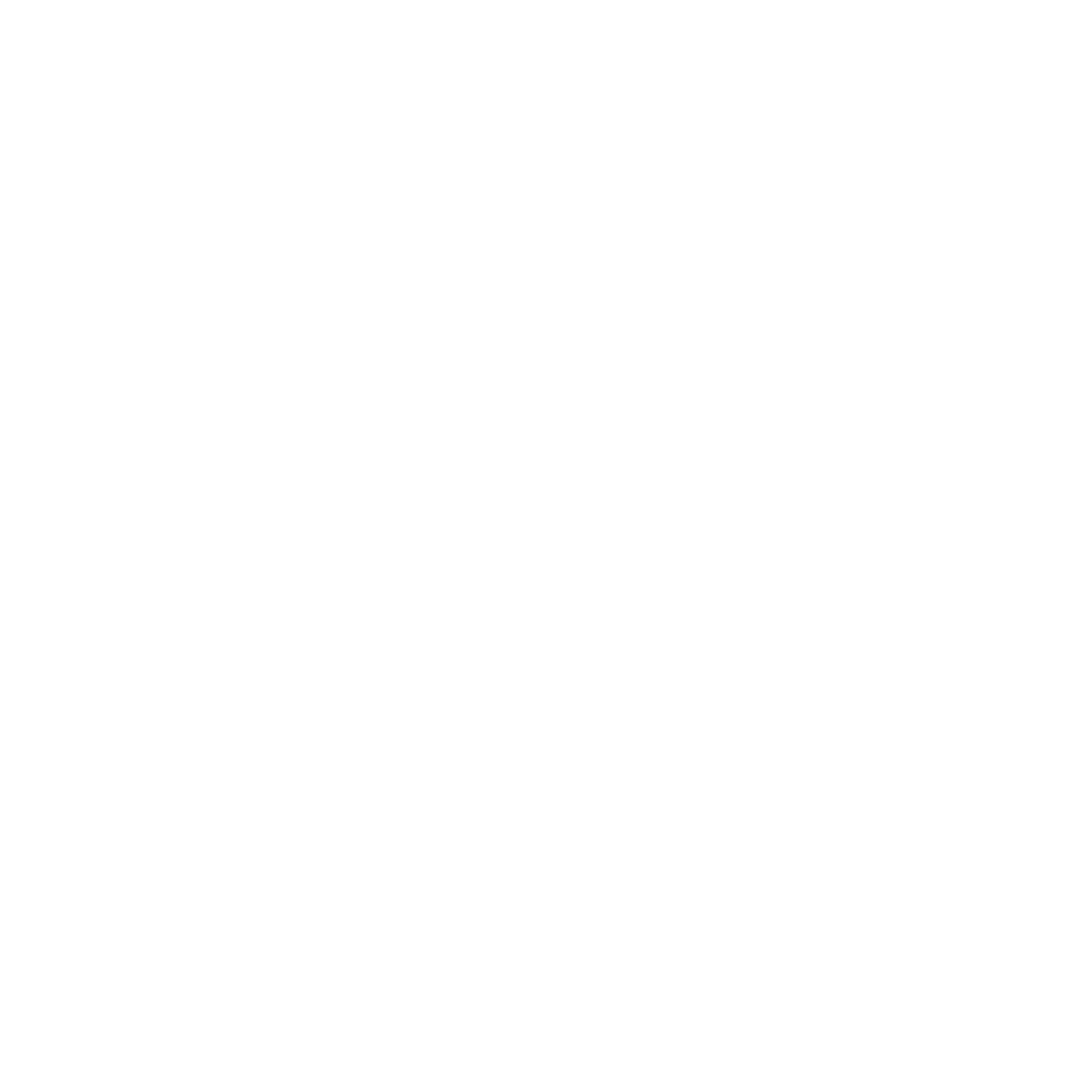一篇流水账——那些流经我的回忆-5
“荒原狼”
在回学校的火车上,邻座两个四川口音浓重的大叔在彼此诉说要回家的兴奋。火车抵达张掖后,其中一位大叔表示,火车驶出酒泉之后就再也看不见荒漠和尘土了,另一位也赶快附和。作为家乡的代言人,我本想为酒泉辩护两句,可在自己所有认知中搜索了一遍,还真找不出反驳的理由。西北的干旱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今年——降水量明显少了,沙尘暴却多了。所有从外地来此的人——无论是工作、旅游甚至是求学都会对此产生极其严重的不适感:打喷嚏、鼻炎、沙眼……

火车上无聊,看起了B站杜素娟教授的推荐书单。一本名为“荒原狼”的书吸引了我。看着窗外的荒滩,我瞬间想起了杨惠显《夹边沟记事》中对70年前夹边沟农场附近荒滩的描写,想到了无人区漫无目的闲逛的狼群。抱着找点认同感的想法,回校第一件事便是借来了赫尔曼黑塞的这本小说,但它给我带来的更多是落差感,然后就是认同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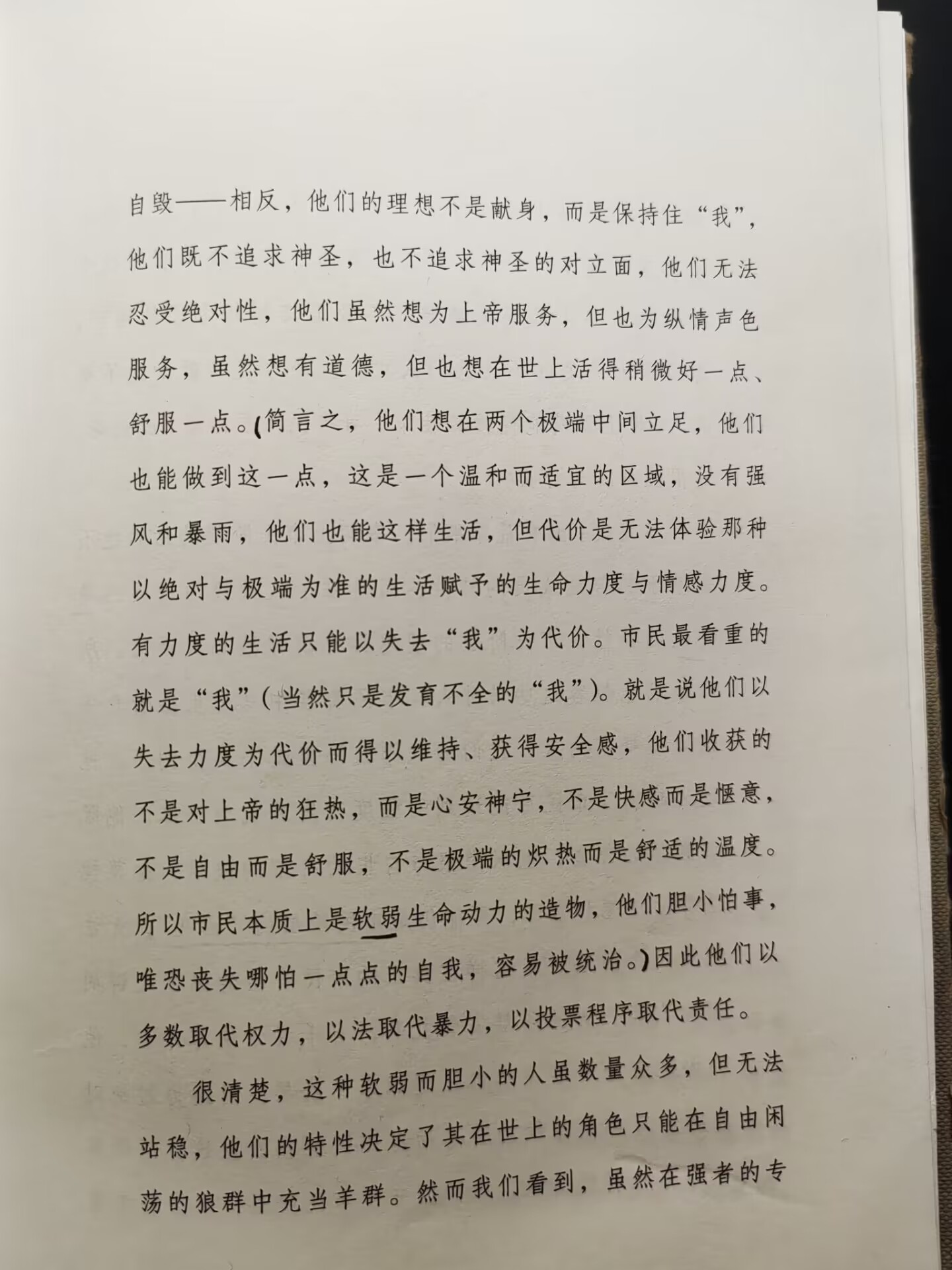
开学第一周很忙,收拾了寝室,考了教资,见了同学,然后就这么过去了。



老东西
暑假时,看到学校的广播站在发招新宣传,我当即就决定加入。原因有二:第一,我需要时刻提醒自己还有这样一个爱好,以免失去热情;第二,我需要满足一种“猎奇”心——招新组一般会将“23级”默认为新入学的那一批本科生,我想看看若是隐藏自己老学长的身份并选择性保留“23级新生”的身份与学弟学妹们相处会怎么样。但没想到,第一次发语音就被识破了。

“老东西”这个称谓在一般汉语语境下通常会被认为是一詈词,但随着互联网中文社区的不断更迭,它似乎被赋予了更多自我调侃的味道。在各大高校的新生群中,总能见到一两个老学长老学姐自称“老东西”,而受到“老东西”们的感染,一些新生们也开始自称“小东西”。
我在广播站的面试十分顺利,第一次面试时更是好好享受了一把被称为学弟的感觉,作为23级”新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学长学姐“们耐心的指导,短暂地体会了一把重返18岁地快感。在第二次面试中,我想到自己身为”老东西“不应该”为老不尊“,更不该”倚老卖老“,于是老实向面试官坦白了自己23级研究生的身份。
还有一次面试,我不得不仔细考虑一下这次我该以”老东西“还是”小东西“的身份站在面试官面前。
周五+雨夜=摸鱼
今日周五,恰逢下雨,空气好到不能再好,温度适宜到不能再适宜。下午临近五点,我在实验室挂机下载数据集,正是百无聊赖时,突然收到了老室友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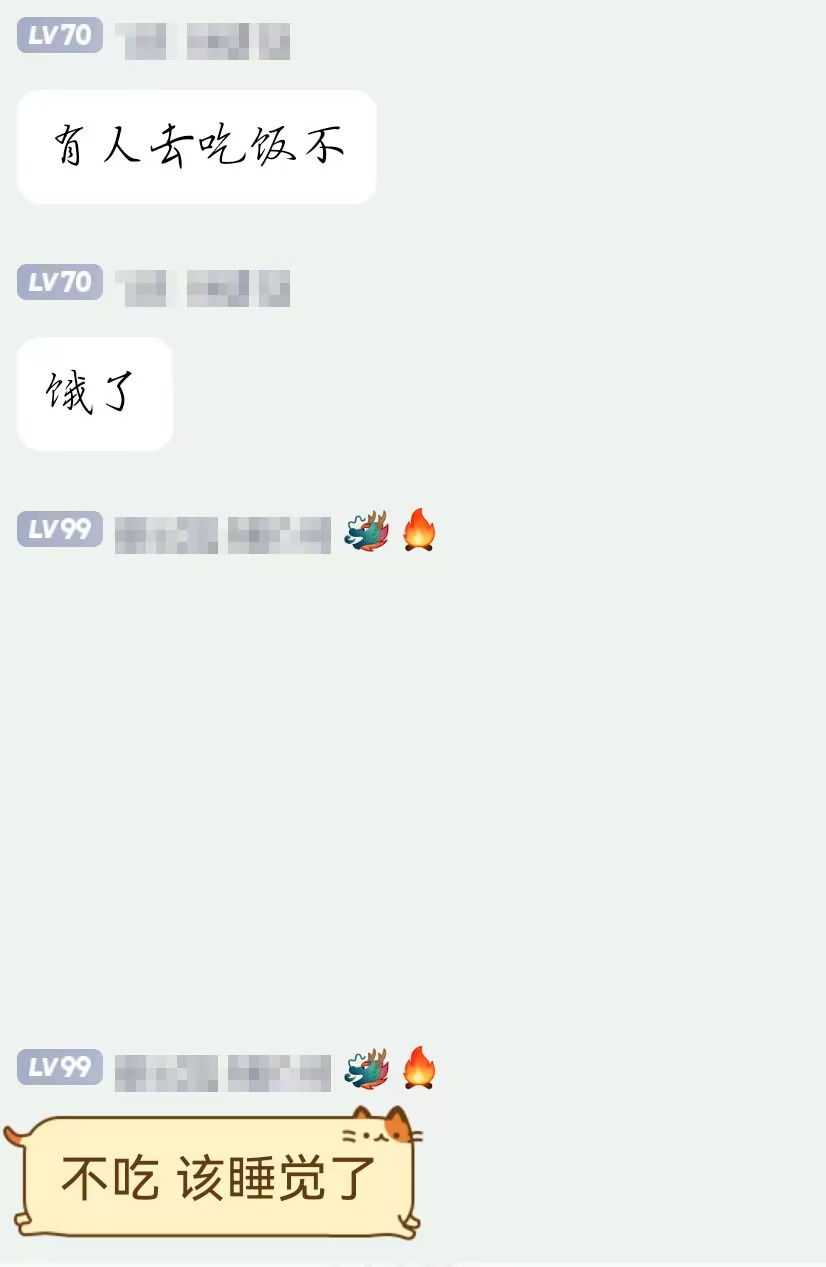
刚好旁边工位的同学也决定直接溜走,于是我也萌生退意。好巧不巧,在给其他同学告别时,恰好被隔壁组老师听到,老师当即就决定向我导“告发”我早退的行为。
虽是玩笑话,但的确让我自责起来。”荒原狼“曾做过这样一个梦:作曲家勃拉姆斯带领着身着黑衣的一堆人像行走于地狱一般前行——黑衣人们是演奏家,大家低着头,共同为自己平庸的演奏赎罪;在一些黑衣人背后,同样也跟着一群黑衣人,他们也在跟着头领赎罪。大家程树形结构,缓慢踱步。
我不得不想道自己,若是有一天冯·诺伊曼、图灵、查尔斯巴贝奇等人出现在了我的梦里,我是否也该穿上黑衣,带上帽子跟在他们后面为自己写过的每一段代码、摸过的每一次鱼而赎罪呢?我不得不按照书中的情节去联想,我想像到了图灵用小腿发出的颤音嘲弄我、冯诺依曼本就不多的头发化作星尘……
我是为了什么而自责的呢?忘记了。不管了,今天是周五,明天是周六。

人与城市
今天注定不是幸运的一天——先是早上出门丢了卡,到工位发现自己一个工作账号被封,中午吃米线还把油滴在了白衣服上。心情郁闷,独自出门走走。
走到天府广场附近,发现一家”星巴克“刚好与一家”蜜雪冰城“并肩开着。前者对我来说已是轻奢,而后者的价格还算亲民;前者门前排着长队,后者门可罗雀(不过大家都坐在里面也说不定)。

在兰州市的地铁二号线完工时,有位老友曾与我交流过他的经历:在地铁新兴的城市,他看到很多人竟然不会乘坐地铁,只会在闸机前独自犯难。我告诉他,在大城市生活久了,自然会把许多东西忽略掉。比如,我国的轨道交通其实只存在于55个城市中(截至2022年12月);再比如,铁路其实无法到达我国的每个地方,许多地方的交通还得靠长途汽车;再比如,疫情期间不会用手机的老人们为了能够生活下去,不得不把自己的二维码打印出来挂在胸前。
没办法,城市的构成如此,抛开个人喜好,有人去喝”星巴克“,也就得有人去喝”蜜雪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