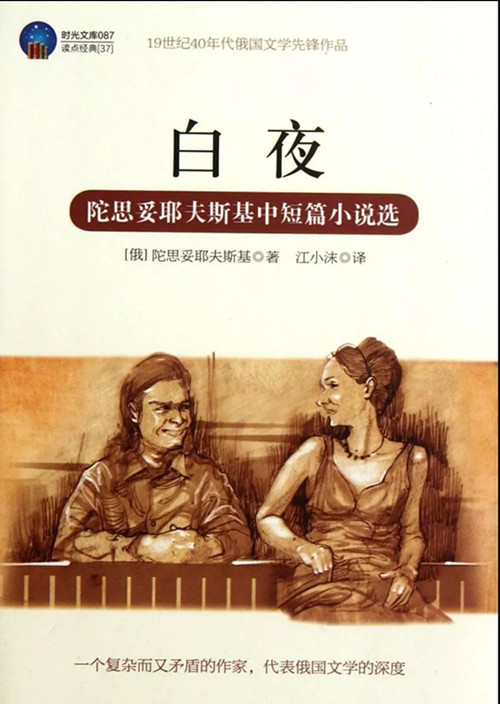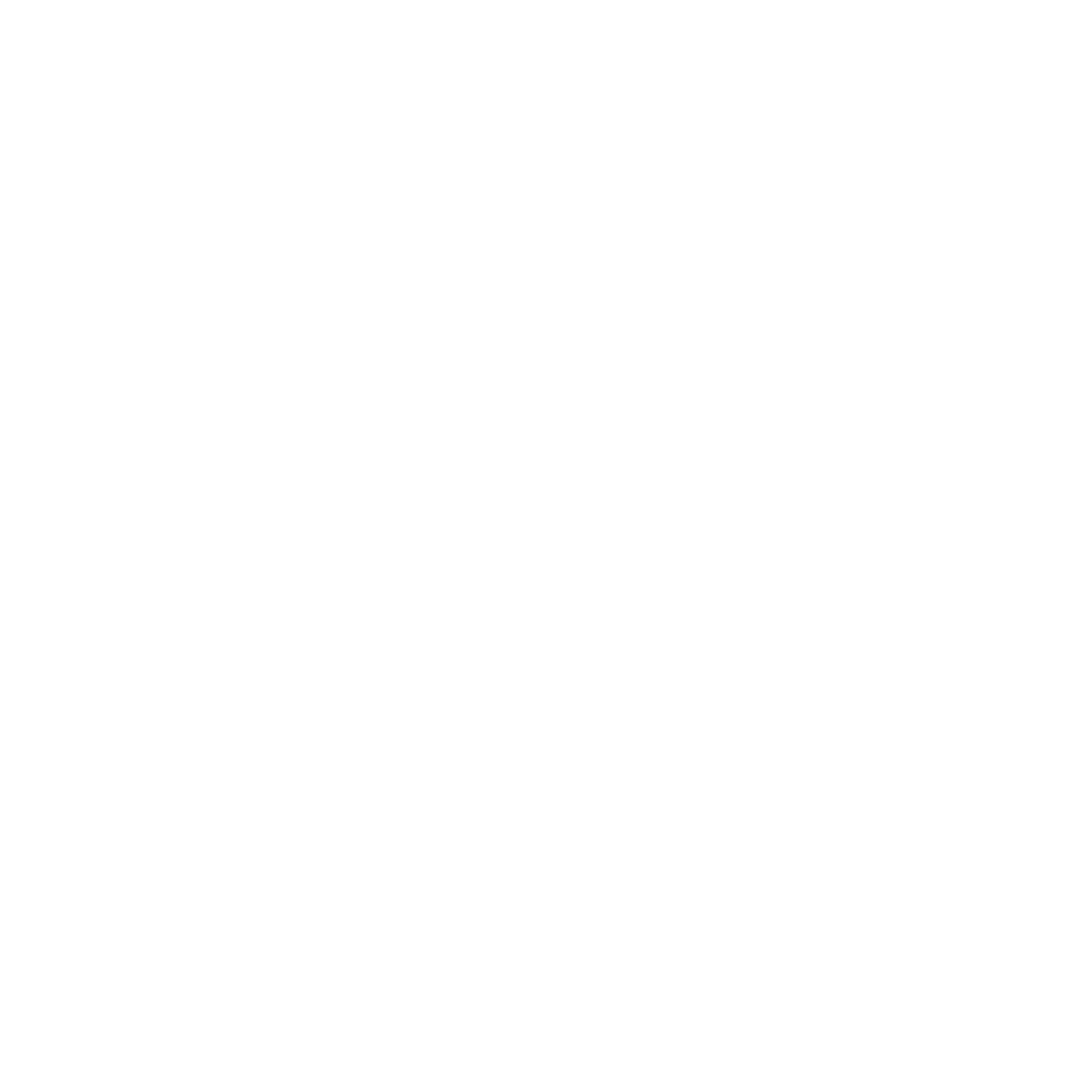用树枝开核桃
电话接通的时候,锡峰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他手里都是未来七天一家人所需的生活物资。人行道上挤满了满载而归的行人,手上、背上,甚至头顶上都是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包装袋。所有人脸上的n95口罩都在剧烈起伏着,但是没有人胆敢在这个关头取下口罩——有人为了防寒,甚至多戴了一层棉质防寒巾。不管怎么说,从明天开始衡泉市又要因为冠状病毒而管控起来,事实上自从几个月前,这样的通知隔一段时间总要在各大小区的业主群传播一次。而各大超市的老板似乎也和大家有了长久配合而来的默契:平时进入超市一定要提供行程码、健康码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三样“通行证”,缺一不可,而在管控前一天仅仅需要其中之一便可。于是,平日里门可罗雀的超市仅仅在这一天有了热闹起来的机会。
“我确定回报考点参加考试,”锡峰答道。“一切后果我会自负。”电话那头的声音略显疲惫,似乎这一整天来一直在打这样的电话,黄昏这一通兴许是最后一通,所有疲惫里还夹着一点点只有在高度紧张后释然才有的轻松。自从锡峰决定要像大多数人一样考研,他已经有很久没有一天睡够六小时了。因为那该死的冠状病毒,直到正式考试前一个月,他还被困在家里,担心自己会因为疫情突然严重而错过考试。如今,尽管很不确定这次封控能否在一周内结束,但锡峰还是决定回到报考点,回到他的大学,完成自己随大流的决心。
一路上,大大小小的商店、小卖部、面馆和理发店大门紧闭,有些店铺拉下了卷帘门,贴上了封条;市中心最大的餐馆门前用十分醒目的红底白字写着“进店需24时核酸阴性证明”,其中数字“24”是用手写的黑字,不久前才被覆盖上去,看起来十分违和。在餐馆入口的门把手旁边,同样贴着大字:“不戴口罩,禁止入内”,从紧闭的玻璃门门看进去,有很多用过的餐具被散乱地堆叠起来,放在一旁,看起来已有很久无人照顾;小区里的柳树枝条已经垂到人的下巴处,已是仲冬时节,它们看起来就像是赶牛用的鞭子,在随处可见的军绿色隔离帐篷上抽来抽去,每个帐篷前都挂着大喇叭,不停重复着冠状病毒的可怕和做好自我防护的重要性。
“大概大部分人都跟我一样吧。”锡峰这样想着。
事实证明锡峰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衡泉市不仅在三天后解除了封控,在他突破层层封锁抵达报考点所在城市后一周,当地政府便宣布不再施行严格的控制措施,这意味着他们这一届大学生因为冠状病毒而冰冻了三年的大学生活终于可以开始流动了。可好消息来得如果太快,也算得上是一件麻烦事——这意味着不少人会因为来不及调整计划而手忙脚乱。学校就像是预见了未来一样,坚决且迅速地发布通知,令大部分同学回家线上学习,所有低年级同学,以及不考研的毕业班同学陆陆续续都离开了学校。锡峰还记得上次离开学校时,校内的八个食堂尚不能满足同学们的需求,吃饭需要排十分钟的队;四百米长桥在东侧吞下下课的学生们,经过漫长的十分钟后,再把他们悉数吐在酉时的黄昏里;教学楼旁正对长桥的通路总是熙熙攘攘,漫长且无序的队伍大有推倒那个写着“出口”牌子的架势。现在呢?仅剩的两个食堂只开放了一层,却鲜有人经过;连通生活区与教学区的长桥被苍白的霾淹没,长久没有生机;只剩下那条小径还不停地有人经过——考研人总得在晨雾散去之前为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落,一个不被打扰,不容易被传染疾病的角落。
“天啊,抗原试纸被炒到50多块了!”晚上,锡峰对着对床的洋葱头说。
“没关系,咱们不一定用得着呢!”洋葱头撇着嘴,蛮不在乎地说。在后疫情时代,同为考研大军的一员,洋葱头的乐观精神总显得格外珍贵。他放下手机,直起身子,脸上带着几分宽慰的神情,表示自己对未来的乐观从未动摇。“你看看,我们现在宿舍食堂两点一线,中招的风险几乎是零!”
”哎,“锡峰翻了个身,半开玩笑半揶揄地说。”咱们要不还是趁着离考试还有两周,别戴口罩出去浪一圈吧!“
”哈哈哈,真是个馊主意!“
”现在阳了,总比考前几天阳了好一点吧。“锡峰说这句话时,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快点呸呸呸!“洋葱头赶忙像锡峰做了个打自己嘴巴的动作。”你盼点好的好不好?天天担心这担心那的,天底下那么多倒霉事,能都让我们给赶上不成?“
锡峰没有说话。最后还是洋葱头打破了沉默:”看看冠状病毒的最新变异株吧,中招的人都成什么样了!怎么会有笨蛋蠢到想主动生病的啊,真是莫名其妙。“大家都没有再说话,这段对话后来似乎也被淹没在平淡如水的生活中——没有人希望这种平淡会被打破,即使是机械式的、简单重复式的平淡,这样若水的平淡足以溺死所有浪漫主义。这一届决心考研的同学最需要的绝对不是学如逆水行舟的毅力,而是漏船载酒泛中流的运气;看着微信朋友圈逐渐被冠状病毒阳性试纸的照片占据,所有人都在默默祈祷着疫情会迟一点在学校里大规模扩散开来,再怎么说也得等到半个月后再说。
可事情不是这样的,在正式考试前三天, 整个寝室都病倒了。就和传闻说的一样,大家失去了味觉嗅觉、不停咳嗽、高烧不退,同时头疼得像是有几头大象在脑袋里蹦迪。大家病倒的第一天,洋葱头趴在桌子上好好哭了一顿,锡峰则一整天都没有下过床;留下的几名考研人共同使用两个体温计,它们的度数一直在39℃上下徘徊着;”疯狂星期四“这天的朋友圈出奇得安静,若是大家还有举起手机打字的力气,各大网络社交平台绝对会充斥着”v我50吃布洛芬“之类的的文案。第一天熬过去,所有人都很感激同为考研人的vv,在大家下不了床时,是他宛如救世主一般带来了退烧药。
幸运的是,考试当天大家恢复了一点应试的能力,虽然尚无嗅觉和味觉,但好歹可以思考了。那天天气阴沉,温度快低至冰点,但学校倒是热闹了许多,人群中夹杂着连续不断的咳嗽声。
“希望运气足够好,碰到个有点人情味的监考老师,能允许我至少带包纸巾进去考试。”锡峰吸了吸鼻涕。“最好再给我备上一杯热水,泡上上好的连花清瘟冲剂。”
“你要不希望下让老师把政治答案写黑板上?这么多要求……”
“嗨,学生做了这么多年,大大小小的考试也考了不少次。这么热血的考试倒是第一次,多提点要求怎么着了?”
“可不是?都烧到39度了,能不热血吗?”在这种话题上,洋葱头很少附和锡峰。
“咱们就像是西西弗斯,推着块大石头上山。眼看要推到山顶了,结果手一滑给滑下去了。”
“就这?还推到山顶?您这会的功夫,顶多把石头推到半山腰!就算你真考上了研究生,后面还有小论文、大论文、小项目、大项目……”洋葱头突然停了一下,深呼了一口气。这样连续地说话已经让他喘不过气了。“算了,咱也别说以后的事情了,就说说现在吧。我考完试,就得赶紧去做毕设了。我给你们讲啊,我之前做了一点调研,试着做了一点实验,我觉得我就跟一大猩猩似的,啥都搞不懂。”
vv拉了一下锡峰的衣角,示意大伙走慢点。
洋葱头自顾自地继续说着。“我的项目就是一颗核桃,而我跟大猩猩一样,在研究怎么把它打开。我手边只有一块大石头和一条和我胳膊差不多长、和铅笔一样粗的小树枝。我先用石头狠劲砸核桃,砸啊砸,砸到石头都碎了,但核桃似乎只是开了个小裂缝。我一气之下,用树枝把核桃从树上挑了下来,它掉在地上,摔碎了。我大喜过望,赶紧在实验报告上写下‘树枝比石头还要坚硬’这样的结果。”
“哦,合着你是把石头搬起来去砸树上的核桃啊?这样能把核桃弄出一条裂缝也是够厉害!”在厚重的口罩下,锡峰发出了几声沉闷的笑。
“大学生毕设嘛,当它能以某种方式运行起来,你就别苛求别的什么了。”
“好好好,无厘头先生!看样子用西西弗斯形容你是委屈你了,你该是堂吉诃德才对!”锡峰说罢,双手作揖,装作毕恭毕敬地对“堂吉诃德”行了个礼。“你是真正的骑士!”
“走吧,冲向风车!”
考完试的这段时间,绷紧的弦没有想象中的松弛,生活依旧被焦虑和迷惘填满。为了准备初试,锡峰自愿放弃了做选调生的机会——他太希望自己能够成功上岸了;在出成绩前的每一天,他几乎都被困在莫名其妙的幻想之中,为自己可能遭遇的每一种失败都找好理由。他耗尽想象力安慰自己,将自己捏造得足够硬核:他想象自己是出海多日,紧紧握着鱼竿的老人,鱼线的另一头连着他这些天唯一的收获——为了这条马林鱼,他耗尽气力与鲨鱼搏斗,可最终上岸时他得到的只有被鲨鱼啃食殆尽的鱼骨;他想象自己是美式短篇小说中的失业员工,试图在得知自己被开除后,独自承担所有精神上的压力,并给自己挑个不引人注目且体面的败法。他深知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终究无法弥补自己思想上的空洞,于是又去法幢寺烧了香、去文殊院请了十八籽,甚至学着西方人一样,背靠着泉眼掷出了硬币。
但他最终也没能如愿,事实上他的遗憾要甚过自己曾设计的所有失败的想象——总分出线整整十八分,但某一科距离单科线差了一分。“Exitus Acta Probat(结果证明行动)”,每次打开手机锁屏,锡峰总能看到这句话。作为锡峰手机锁屏问候语,它陪着锡峰完整走过了四年大学生活——太正确不过了,人们爱吃苹果,可没人在乎果树在结果前农夫为它浇了几次水,施了几次肥;决定一个学生去向的也只有一次考试后的得分,老师们可不会在乎学生为了考试记了多少单词,刷了多少数学题,有多少个未眠的夜晚都在背政治要点。“命运就是这样的。”在去参加双选会的路上,锡峰这样想,为了让自己看起来精神点,好紧紧抓住每个拯救未来的机会,锡峰甚至穿上了自己唯一一件浅色的衣服。
“上五休二,早九晚五,午休撸猫!”
“工作轻松,包吃住!”
……
招聘会就被设置在学校广场上。所有与会公司都搭着小帐篷,帐篷下设置一张课桌,桌子的一边放着两张椅子,另一边只放一只椅子;为了宣传自己,很多公司甚至用扩音器吆喝起来,自打学校开学时为各大社团举办的招新活动结束后,这样的热闹场面还是第一次。锡峰自顾自看着人山人海,完全没有注意到迎面走来的一位同学,他和锡峰一样穿着亮色的衣服,手里拿着一堆打印好的简历,也正自顾自地整理文件;无暇顾及路况的俩人就这样撞上了,无辜的同学简历散了一地。
“对不起对不起!”锡峰一边说着,一边帮忙捡起散落的文件。
“哎,你和我居然是同一个专业的?”
“是啊,这不是没考上研,来投简历了嘛。”
“嗨!同是天涯沦落人!”
同为失败者,似乎真能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他们就像是多年未见偶然重逢的密友,无话不谈。锡峰向被撞倒的同学讨要经验,而那位同学也知无不答。锡峰从这里了解到:西区的企业只招硕士;东区的几个企业只要同学院的另一专业;而北区的企业是几个金融和保险公司——和锡峰的专业完全不搭边,但锡峰还是决定去投几份简历;只有南区的几个帐篷前排着长队,不少人在队伍里焦急地等待着;那位同学起初不愿意接受离家,后来却还是给离家千里的单位投出了简历,据他自己说,和那边能占自己收入60%的房租来说,距离不是最该担心的……
对话是被锡峰收到的一条短信打断的,那是锡峰的老妈发来的短信。信的内容倒也简单,除了劝儿子早点去找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其他的便是自责——似乎锡峰在单单一个科目上失去的那一分与她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又或者说在责备自己没能给自己的孩子更好的去处——一个除了随大流之外的去处。寥寥几笔,却能感觉到发短信的人推敲了很久才最终按下了发送键;区区几眼,读信的人便立刻锁屏了手机。锡峰不知道该不该给妈妈打电话回去。
广场边上是校园里各色各样的花坛,正是孟春时节,里面开满了时令的花。淡蓝色的蝴蝶兰、浅黄色的金鱼草,还有很多不知名的花草,被整整齐齐地按照花坛的形状分区摆放;离远了看,各花坛连起来,像是床单上的花纹被条纹分开,却又连成一片、彼此融合的图案。虽美的整齐,但小小学校花坛里的花是注定不能能被更多人欣赏的,虽然同样美得整齐划一,但它们终究比不过市政广场中心花篮里的花朵那样引人注目。锡峰坐在花坛边上,浅黄色的衣服也和金鱼草丛融在了一起。
在春天混沌的夕阳里,锡峰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写在最后:本文是对理查德·耶茨《十一种孤独》写作风格的一次拙劣模仿,文中所有人物均是作者身边很多同学形象上的杂糅。关于23届考研这事,若是好结局,也实在不能被当作鼓舞人心的励志故事;若是结局并不能让人满意,也不该成为阻止你向前走的障碍。用《圣经》的一句话做结尾吧,希望每个人在人生每个阶段的最后都能收拾好心情再出发。“I have fought the good fight, I have finished the race, I have kept the faith.”)